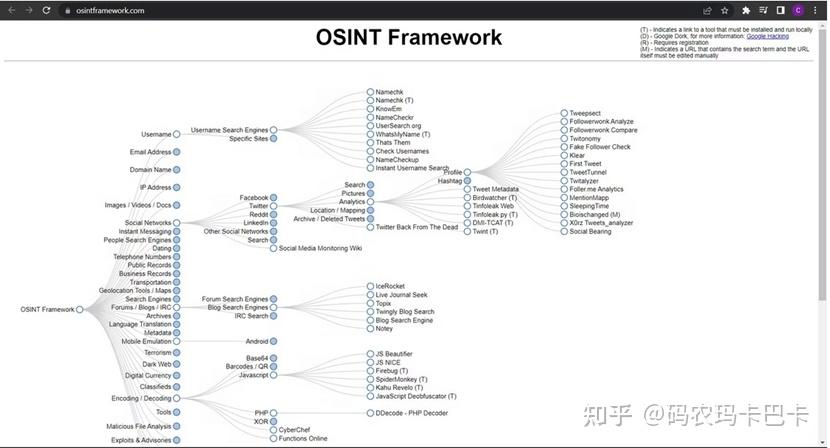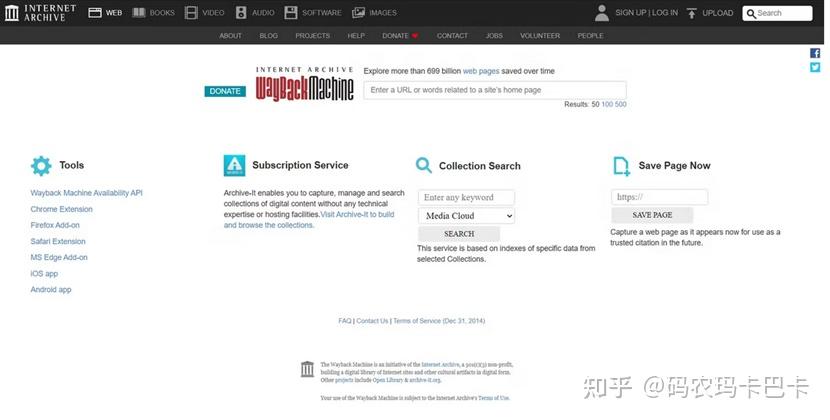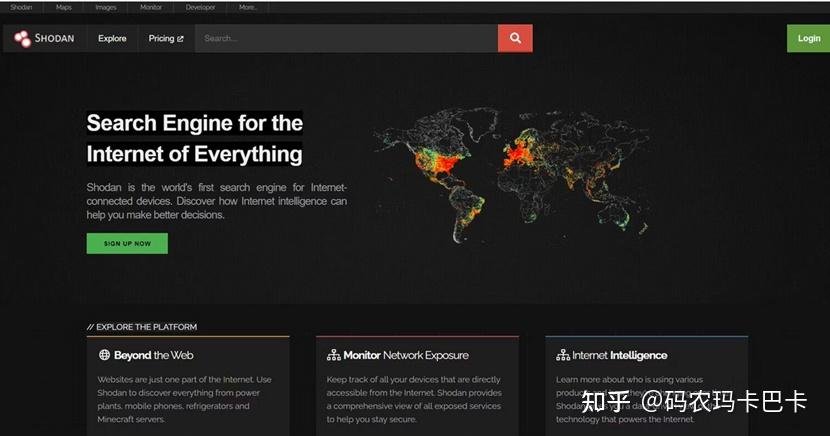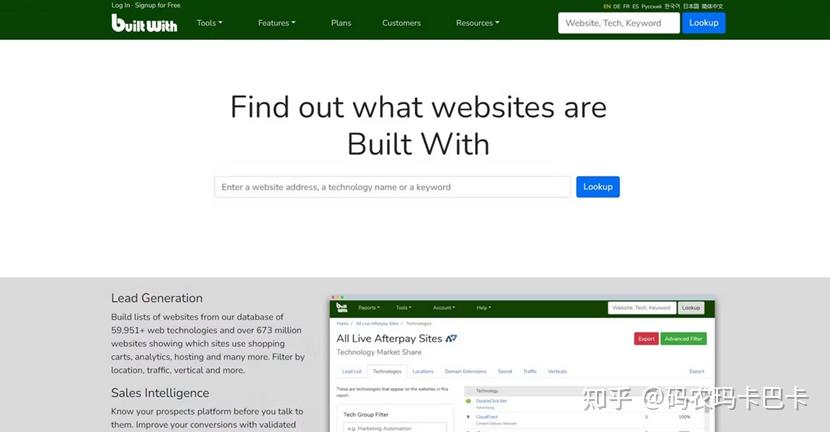乔治·沃尔德
于1970年
这可能是我父亲最伟大的科学演讲,它完美地平衡了真正的探索性的科学思想和一种流行的演讲风格,这种风格使他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中获得了美国二十位最伟大的教师之一的地位。我希望我能包括他用来展示的幻灯片,它们从科学图表到《纽约客》的漫画不一而足。
当一个人多年来对生命的起源感到好奇,就像我一样,一个不可避免地会问自己,一个试图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那些在地球上的第一批原始生物,比如说,是否需要拥有像今天所有生物一样复杂的繁殖器官?然后一个人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那些第一批生物是否需要死亡?因为如果它们不需要死亡,它们至少不需要那么急于繁殖。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死亡起源的问题。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会死亡。例如,变形虫永远不需要死亡;它甚至不需要像某些将军一样,慢慢消失。它只是分裂成两个新的变形虫。
事实上,死亡似乎是进化中相当晚的一项发明。在进化的漫长过程中,要遇到一具真正的尸体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就是我想和你们一起做的旅程。我想做的,当然,是从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生物开始,然后继续追寻进化的脚步,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养成了死亡习惯的生物?但这正是我不能做的。就像在许多其他的进化故事中一样,我只能满足于一件更差的事情,那就是用当今的生物,用今天活着的生物来讨论这个转变。
让我们从一个熟悉的单细胞生物,变形虫开始。它的细胞核通过捏合成两个相等的一半,然后整个变形虫分裂。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物,而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这是单细胞生物,植物和动物,倾向于繁殖的通常方式,就是简单的分裂:所谓的裂变。
有时它们会做一些有点不同的事情。单细胞生物草履虫的繁殖通常是通过裂变,但有时它会进行我们所说的交配。两个生物,每个都包含一个大的细胞核(大核)和一个小的细胞核(小核),侧面相连。然后它们之间的外壳分解。大核基本上是工作核。小核代表了一种遗传物质的储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大核分解,小核分裂,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让人想起了一点性繁殖:有小核,有遗传物质的交换。然后草履虫分开,小核反复分裂,然后草履虫反复分裂。最后得到了八个全新的草履虫,就像我们开始的那一对一样。
在我这一代之前,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动物学家,名叫洛兰德·伍德拉夫。他开始发表一系列的论文,第一篇的标题大概是“两百代草履虫金色品种没有交配”。我们等了几年,又出来了一篇标题大概是“五百代草履虫金色品种没有交配”的论文。最后这一系列达到了高潮,发表了一篇标题是“一万一千代草履虫金色品种没有交配”的论文。所以伍德拉夫教授过了一生幸福而有用的生活,并说服了我们所有人,草履虫可以无限期地不交配而生存。
但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伍德拉夫又发现了另一件事。你看,每天早上他都会来到实验室,发现两个草履虫,而他前一天晚上只留下了一个;所以他就小心地把它们分开。他认为,一个草履虫是不能交配的。但这就是他被骗了,因为他如此专注地观察这些草履虫,他发现了这个过程中还有第三种变化,他称之为内混合。这是一种自己动手的交配。在内混合中,草履虫的大核分解,小核分裂,其中一个新的小核长大成为一个新的大核,你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草履虫。
然后还有第四种过程,非常有趣。它叫做合子形成。在合子形成中,两个细胞融合成一个;这当然是性繁殖中发生的本质。所以,这里我们有了,仅仅在这些单细胞生物中,四种不同的繁殖方式,但没有必要的死亡,没有尸体。
现在让我们在进化中做一个巨大的跳跃,到一个低等无脊椎动物,海葵。我们从一个单细胞生物跳到了一个非常多细胞的生物。它不是很高度的专化,只有两层细胞,而我们有三层。它只有外胚层和内胚层;我们还有中胚层。它是放射对称的,我们认为这比我们的双边对称,我们的两面性,要原始得多。然而,这是从单细胞生物跳跃的一个大进步。海葵从中间分裂,通过简单的分裂,简单的裂变来繁殖。
这种过程在这个水平的生物中是一种习惯。一个近亲,水螅,通过萌芽来繁殖。一个芽长大,最后从母水螅分离,开始了一些新的水螅。
接下来我们在生物的等级中又做了一个巨大的跳跃。我们有一种扁形动物,叫做涡虫。这种动物是双边对称的,就像我们一样。它有三个胚层,就像我们一样。它的神经系统集中在头部。它有相当好的感觉器官。它代表了从水螅和海葵跳跃的一个大进步;然而我们看到这种生物通过简单的分裂来繁殖。它在腰部捏紧,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然后再生它所缺少的东西——尾部培养一个新的头,头部培养一个新的尾,结果是两个全新的扁形动物,而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许多扁形动物经历这种过程。有一种叫做切口虫的,会分成五六个碎片;然后每个碎片再生它所缺少的东西。
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慢慢消失的生物,那就是涡虫。许多年前,有一位荷兰的工作者,名叫斯托本布林克,开始饿涡虫。当他饿它们的时候,它们开始消耗自己的物质,遵循一个确定的程序。首先它们吸收了所有的性产品。然后它们开始消化自己的消化系统,这对它们来说反正也没什么好处。然后它们开始吸收自己的肌肉。这样,扁形动物变得越来越小。它们唯一没有吸收的是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当它们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很聪明——全是脑,没有虫。这时我已经喘不过气来,等着读到斯托本布林克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刻,瞧!再也没有扁形动物了。但令我非常失望的是,他反而开始喂它们,它们很快就再生了它们所失去的一切。然而,斯托本布林克发现了一件事;因为你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扁形动物。他发现,如果你定期地饿扁形动物,然后再喂它们,它们就会永远活下去。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道德寓意。
我能够追寻的通过简单分裂繁殖的方式最远的是到了真正的蠕虫,和我们常见的蚯蚓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有一种有着美丽名字的蠕虫,叫做分裂线虫,它根本没有性器官。它完全是通过分成许多碎片来分裂的;然后每个碎片再生它所缺少的东西,你就有了那么多新的蠕虫。
但在这之前,生物已经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繁殖方式,性繁殖;而死亡正是与性繁殖的方式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出现在舞台上的。
我能够最好地用十九世纪一位杰出的动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所描述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任何一个通过性繁殖繁衍的生物,都是从一个单细胞,一个受精卵开始它的生命。这个单细胞反复分裂,最终成为一个成年的生物。在它的许多分裂过程中,有一条细胞线构成了魏斯曼所说的生殖细胞系,它最终会产生成熟的性产品,卵子或精子。在这些反复的分裂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身体,魏斯曼称之为体细胞系。在性成熟时,这个生物将它的卵子或精子与另一个相似的异性成年生物的卵子或精子混合;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新的受精卵,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反复的分裂,产生了性产品和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在成熟时,又将它的性产品与另一个成年生物的性产品混合。这样你就有了下一个受精卵,它通过反复的分裂,产生了下一个成年的一代。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
在这个简单的基础上,奥古斯特·魏斯曼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则。他把第一个原则称为生殖质的隔离。我想我们现在会这样说,遗传信息总是沿着一个方向传递,总是从生殖质传递到体细胞系;从来不会反过来,从体细胞系传递到生殖质。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有后天性状的遗传。后天性状是身体,体细胞系的变化,而没有办法把这种变化传递到生殖质中,从而遗传。
魏斯曼提出的另一个原则,他称之为生殖质的潜在不朽。你看,生殖质继续制造更多的生殖质和身体。生殖质的线条没有中断。现在我们看到了死亡是什么。死亡是在身体,体细胞系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把它抛弃。它的工作就是携带生殖质,给它提供食物,保护它,给它温暖,在一个温血动物中,最后把它与异性的生殖质混合。这样,它就完成了它的功能,可以被丢弃。
这种一旦完成了性繁殖,生命就对身体不再需要的想法,对我们作为人类来说是令人反感的。我稍后还会再谈这个问题。然而现在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否令人反感,这对一条鲑鱼来说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在鲑鱼,鳗鱼,和许多这样的生物中,繁殖是生命的最后一幕,而准备繁殖同时也是准备死亡。
我想谈谈这样一种动物,七鳃鳗。所谓的海七鳃鳗可能对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太熟悉,但对我们沿海的人来说却很熟悉。这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七鳃鳗的形状像鳗鱼,常被称为七鳃鳗鱼,但它们不是鳗鱼,甚至不是鱼。它们属于最原始的活着的脊椎动物的一个小群体,无颌脊椎动物或无颌类。它们没有颚,只有一个吸盘,上面有一种粗糙的锉刀。当它们有机会的时候,它们就用那个吸盘把自己附在一条鱼上,然后开始锉进去。如果是一条足够大的鱼,而且鱼能坚持住,七鳃鳗可能最终会完全钻进去。这种事情在五大湖里发生了很多,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知道,因为挖了一条运河说服了七鳃鳗,不要像以前那样下到海里去,而是进入五大湖。有一段时间,它们几乎把整个五大湖的渔业都清理干净了。
七鳃鳗的生命开始于一个虫状的幼虫,没有眼睛,埋在一条急流的泥沙中。它就这样呆了大约两三年。然后它经历了第一次变态,其中,除了其他事情,它获得了眼睛。有了这个,它就从泥沙中出来,开始向下游迁移,通常到海里,长大。在性成熟时,它经历了第二次变态。有很多变化,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消化系统的完全分解。这种动物再也不会吃东西了;它失去了整个消化食物的器官。然后它开始向上游旅行。
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河里捕到了我的七鳃鳗。一个水力发电开发和一座大坝已经建在河上。埃克塞特的好人们已经世世代代地把瓶子和罐头扔到大坝下的水里。水不多,而且很危险,但那些七鳃鳗还是在春天的第一天温暖的时候上来了。它们是怎么越过大坝的,我不知道。我怀疑它们走到了岸边,因为这些动物在性迁移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在脑子里,那就是要到达它们的产卵地。在那里,它们用圆石做了一个巢,雌性在巢里产卵,雄性在卵上释放精子,就这样,它们结束了。所有的成年七鳃鳗都死了;对它们来说,生命中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淡水鳗鱼的生命周期正好和七鳃鳗相反。它是由一个伟大的丹麦海洋学家,约翰内斯·施密特,在许多年前发现的。在那之前,鳗鱼在哪里繁殖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谜。大西洋沿岸的鳗鱼有两种不同的物种,欧洲的和美国的。它们都聚集在马尾藻海的重叠区域产卵,马尾藻海是南大西洋的一个地区,包括百慕大。它代表了大西洋最深和最咸的部分。经过了这样一次巨大的旅行,成年的鳗鱼产卵并死亡。然后小鳗鱼独自回来。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回来的。美国的鳗鱼大约需要15个月才能回到我们的海岸,变态,然后向上游前进。欧洲的鳗鱼需要三年才能回到家。目前还没有任何小鳗鱼弄错方向,去了错误的地方的记录。当它们进入淡水时,它们在那里生活五到十五年,长大。然后在性成熟时,它们经历了第二次变态。有很多变化:眼睛膨胀到原来的两倍,原来的四倍。这种动物正在为一次深海之旅做准备。在开始之前,它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在这些生物和其他许多生物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繁殖是生命的最后一步,而为了繁殖做准备,同时也是为了死亡做准备。
有时候,死亡不会等到繁殖的行为完成,而是参与其中。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昆虫观察的黄金时期。我们有法国的亨利·法布尔,瑞士的奥古斯特·福勒尔,英国的约翰·卢博克爵士,还有比利时的莫里斯·梅特林克,他写了关于蜜蜂的生活。当这些生物学家如此专注地观察昆虫时,大家对螳螂的习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螳螂是一种贪婪的动物。它会攻击比自己大得多、强得多的东西,而且通常会赢。有人观察到,当一对螳螂在交配时,雌螂,它是一种更大的动物,有时会轻轻地转过它美丽的、像茎一样的脖子,悄悄地开始吞噬雄螂。雄螂继续交配,而雌螂继续吃他。只要雄螂的最后两个腹部节还在,他们就继续交配。
几年前,我去拜访了我的好朋友,塔夫茨大学的肯尼思·罗德教授。当我到那里找他时,一个学生告诉我,“你会在那条走廊的最后一扇门右边找到罗德教授。”于是我走过去,发现肯·罗德坐在一个肥皂盒上,看着螳螂。他给我另一个肥皂盒,我们一起坐在那里,一起观察。他告诉我,他已经这样做了好几年。他告诉我,如果你把一只雌螂单独放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放进一只雄螂,那只雄螂会立刻僵住。螳螂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比如青蛙,似乎只有在东西动的时候才能看到。雄螂知道这一点,他非常小心地看着雌螂。如果她一瞬间把目光移开,他就会急忙向前迈出几步。然后她一回头,他又马上僵住。罗德说,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如果雄螂幸运的话,他会到达雌螂身边,登上她,进行正常的交配。顺便说一句,罗德告诉我,一旦美国的雄螂开始交配,雌螂就不会再打扰他。这是我们更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往往雌螂先看到他。于是,她抓住他,总是从头开始。然后她开始吃他,总是从头开始。一旦她把头吃掉了,雄螂就进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行为模式。他把前脚稳稳地立在地上,开始绕着它们转圈,同时做着剧烈的交配动作。这样,罗德告诉我,一个没有头的雄螂经常会成功地登上雌螂,进行正常的交配。
肯·罗德是一位杰出的神经生理学家。他渴望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最终弄清楚了。在最后一个腹部节里有一个交配中枢。但是在颈下神经节里有一个抑制中枢,它抑制了交配中枢。这一切都很简单。你不需要一只雌螂来解除这种抑制。罗德用一把剃刀刀片切掉了头。一旦雄螂失去了头,交配中枢就被释放了。所以这是一个杀死雄螂有助于刺激繁殖行为的例子。
在哈佛,我们有一个安排,让有兴趣并且看起来能胜任的本科生,在最后几年开始做研究。几年前,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孩来找我做毕业研究。我刚刚在动物室里发现了几十个活动笼子,没有人在用,所以我把两件事加在一起,为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孩想出了一个美妙的问题。
活动笼子就是一种笼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生活区,通常有食物和水。老鼠可以在那里安然生活,但是它们随时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开门,进入一个非常精心平衡的跑轮,如果它们想的话,可以跑一跑。当它们跑完了,它们就回到生活区,吃点东西,然后睡觉。当它们醒来,它们就进入跑轮,跑一会儿,然后出来,吃点东西,睡觉。这就是大多数动物,包括老鼠,度过一天的方式。这样的老鼠跑步并没有什么目的。它们就是这样做。一个正常的动物可能一天会跑两到六英里。
生活很早就让我接触到了维生素A——但有时候我会有点不安分,想要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做点关于维生素B的事情呢?就在那时,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孩出现了。
我不打算冒险,我打算从维生素B1,硫胺素开始。硫胺素是一种重要的维生素。世界各地的制药公司都必须准备好估计各种食物中含有多少硫胺素。我不太清楚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会养满一间间的老鼠。他们会把一群老鼠放在缺乏硫胺素的饮食上,让它们发展成老鼠多神经炎,这是老鼠的多神经炎,是人类所说的脚气病。每天早上,一群女孩会进来,穿上白大褂,沿着笼子一排一排地走。她们会拿起每只老鼠,给它做一个旋转测试:她们会抓住老鼠的尾巴,把它举过桌子,旋转一下,然后放下。如果你这样做给一只正常的老鼠,它只会给你一个不满的眼神,然后跑开;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给一只开始缺乏硫胺素的老鼠——多神经炎的老鼠——它会很难恢复平衡,重新站起来,这是多神经炎的第一个迹象。一旦你看到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给这些动物喂各种食物,估计它们含有多少硫胺素。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想,如果我们把老鼠的硫胺素拿走,当它们进入多神经炎时,它们当然会停止跑步。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早期的、定量的硫胺素缺乏的迹象。
嗯,这就是我被骗了的地方。我最近没有听到过有人引用它,但我们经常互相引用我们所谓的“哈佛动物行为法则”。它说,“在最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动物会随心所欲地做事。”这正是这次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把这些老鼠的硫胺素拿走时,它们不仅没有停止跑步,反而开始拼命地跑。它们日夜不停地跑,有时候会跑出它们正常跑步的四十倍。与此同时,它们还在减肥。有时候,虽然我们努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还是会发现一只老鼠死在跑轮里。计数器会显示,它在前一夜里,不知怎么地挣扎出了最后一英里。
嗯,这似乎很不寻常,也让我们很兴奋。所以我想,维生素B2,核黄素呢?如果你把核黄素从合成饮食中去掉,老鼠又会开始拼命地跑。如果你拿走它的水,老鼠会跑;如果你拿走它的食物,老鼠会用跑步来回应。如果你把它的食物和水都拿走,它也会跑——虽然你不能这样做很久,还能保住一只老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被告知,通常是被某个正要掏我们口袋的人,自我保护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这里的动物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规则。如果这只动物只是在笼子的一个角落里睡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孩可能会结婚;或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实验感到厌倦。这些动物只是在自杀。
这让我深入地研究了文献;然后我了解到,从原生动物(那些单细胞动物)到人类,所有动物真正缺乏食物的普遍迹象,就是活动增加。你可能会想:这些动物在寻找食物。但它们不是;它们只是被驱使着跑。在这种实验的全盛时期,人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把动物的胃拿走了。你的饥饿感觉只是对上部胃的一种深而缓的收缩,叫做饥饿收缩的反应。这些动物的行为就像其他动物一样。你可以把动物的大脑皮层拿走。这样的动物无法识别食物;但是当它饿了,它就跑。它不能自己喂自己,但是如果你把食物塞到它的嘴里,它就吞下去,这样就喂饱了。然后它就睡觉,然后它就醒来,跑到再次被喂饱为止,然后它就睡觉。我们的老鼠不是在寻找食物。这样一个饥饿的动物不是被要求跑,而是被命令跑。这些是命令,不是请求。它们被迫跑。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有一种小规模的模型,用来解释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一种饥饿迁徙。饥饿迁徙中最著名的,你们都听说过的,就是旅鼠的迁徙。旅鼠是一种生活在挪威山坡上的啮齿动物。关于这一点有一种神话,说在旅鼠年,旅鼠以成千上万,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从山上下来,肆虐城市,把人们赶到室内,阻碍所有的交通。它们在去海洋的路上。当它们到达海洋时,它们就跳进去,在一次集体自杀中,游走,再也没有出现过。
嗯,事情并不完全是那样的。旅鼠是一种相当可爱的,但不合群的生物。一个旅鼠通常只能容忍另一个异性的旅鼠。当这样的一对,一起旅行,遇到另一对时,它们就会互相咆哮,然后各走各的路。挪威的形状是这样的,对于从山坡上漫游的动物来说,很多都会到达海洋;而且的确有很多都会进入水中,游走,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它们并不是在寻找海洋。在同一座山的另一边,同样的旅鼠也会到达拉普兰的平原,然后在那些平原上漫游,直到死去。
这就是重点。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清楚,这种迁徙是由饥饿驱使的。它发生在一个超过了资源的人口中。动物们饿了,而一个饥饿的动物必须跑。它被驱使着跑。它不是在寻找什么。它只是不得不一直移动。你可能会认为,这种饥饿迁徙的目的是殖民。你可能会认为,这样一群饥饿的动物离开它们的家园,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但是没有这样的地方。如果有更好的地方生活,它们早就找到了。它们没有地方可去。饥饿迁徙的目的不是殖民,而是移除迁徙的动物。每一次饥饿迁徙的终点,都是迁徙动物的死亡。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把人类也包括在这种模式中。你可能会说,“嗯,我饿了不会到处跑。”那是因为你被说成是文明的。这会妨碍各种合理的模式。如果你想看到人类表现出这种方式,你必须在他们原始的时候抓住他们。
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方法是观察一个婴儿。每一对年轻的夫妇都知道新生儿是什么样子。它就是经典的动物模式。一个新生儿醒来,开始扭动,大声哭叫,脸变得通红,充满了活力。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然后你开始喂它。通常它会在喂食的过程中睡着。你必须不停地拍它的屁股,才能让它吃完。然后它睡一会儿,然后它醒来,扭动和哭叫,又要被喂食。这就是它开始生活的方式;直到那对年轻的夫妇把它教化成每隔八个小时睡一次。
要抓住人类原始的状态,另一种方法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我非常怀念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最便宜的实验动物是医学生。研究生更好。在过去的日子里,如果你给一个研究生提供一种缺乏硫胺素的饮食,他会很高兴地接受,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吃的方式。科学变得越来越困难。
几年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柯特·里希特教授的实验室里,他给一群医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凡的特权,就是在实验室里有一张床。有一些手续:在医学生上床之前,他要吞下一个气球,气球连接着一根橡皮管,橡皮管从他的嘴里伸出来,连接着一个水银压力计,它会记录他的胃在整个夜晚的运动。然后,那张床不是一张普通的床。它是非常精心平衡的,这样,如果那个医学生在睡觉的时候动了,那也会被记录在一个旋转的鼓上。嗯,就像经典的模式一样,一个四小时的周期贯穿整个夜晚,医学生的胃会开始进行缓慢而深的饥饿收缩。当它们达到顶峰时,医学生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饥饿收缩会消退,医学生又回到安静的睡眠,直到四个小时后,他又经历了同样的周期。
至于人类的饥饿迁徙,赫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段美妙的段落,用经典的形式描述了它。赫罗多德在描述希腊运动会的起源,我们现在称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在马涅斯之子阿提斯的统治时期,吕底亚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它一年又一年地持续下去。经过七年,国王规定所有的人必须每隔一天进行体育运动,另一天吃东西。又过了七年,饥荒仍然持续,国王把人口分成两半,一半迁徙,另一半留下。这最终把我们带到了人类。
我们认为旅鼠的集体自杀是一种反常的行为,是一种心理病态的行为,这有点奇怪;而我们处理同样问题的方式却被认为是正常的。旅鼠去死,我们去杀;对于人类的迁徙者来说,也同样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每个地方都有人。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人们迁移到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而那里以前没有人?总是有人。如果迁徙以殖民为结果,那是通过征服。我们认为这是正常和合适的,而旅鼠似乎在做一些反常的事情,这很奇怪;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旅鼠的做法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方面,旅鼠的方式,死亡的数量最少。只要有足够的旅鼠离开了人口中心,留下的旅鼠就有足够的食物,所以迁徙就自动停止了。第二,没有破坏。旅鼠的家园和以前一样好。第三,每当我说这个,我都会不寒而栗,因为我不能跳过自己的影子,但是这里有一个选择过程在起作用。是最饿的旅鼠去死;那些过得更好的旅鼠留在家里。而在人类做事的方式中,我们挑选我们的精英去杀和死。旅鼠在实践更好的生物学。
我现在想回到那个令人厌恶的想法,那就是一旦繁殖完成,生命就和动物无关了。这对人类来说是不正确的。为了缓解这种情况,通常的做法是,每当一个人描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时,他就解释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正确的,让我来谈谈蜜蜂。你们都知道,蜜蜂群中发生的一切的核心,是工蜂所做的事情。工蜂建造蜂巢;它们照顾幼蜂,寻找食物,清理蜂巢,运行空调系统,等等。它们做所有的事情;而它们却是没有性别的雌性,没有参与繁殖。蜂巢里唯一有性别的雌性是蜂王。这就是重点。如果像蜜蜂这样的动物有一个社会,那么个体就可以为那个社会的目的服务,而它们是否繁殖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们人类有一个社会,我们就是这样。贝多芬,据我们所知,没有孩子;巴赫有很多。谁在乎呢?这不是我们去听贝多芬和巴赫的原因。伦勃朗有一个儿子;艾萨克·牛顿没有孩子。谁在乎呢?这完全无关紧要。对于有社会的生物来说,这变成了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自从我们有了历史,人类就追求一种不朽的理想。我现在说的不是灵魂的不朽——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而是肉体的不朽,身体的不朽。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找哲学家之石,青春之泉,所有那些试图消除死亡的努力。
这种对肉体不朽的追求是一个骗局。彼得·梅达瓦有一本书叫《个体的独特性》,在它的前两章,你会找到这一切都被阐述出来。梅达瓦指出,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所有人想要的肉体不朽的特征,那么它会对我们现在的状态改变很少。正如梅达瓦所说,我们都想长大,所以让我们能够达到大约20岁,然后永远不再变老。然后他补充说:让没有自然死亡。梅达瓦说,他在这一点上有点担心,他开始四处询问他在伦敦的所有医生朋友,他们是否曾经看到过一个人死于老年。我们都带着熟悉的概念,死于老年,自然死亡。结果是,他认识的医生中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想,如果一个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写上老年是死亡的原因,他会被工会赶出去。总是有一些最后的事件,一些器官的衰竭,一些最后的肺炎发作,结束了一个生命。没有人死于老年。不过,梅达瓦说,没有自然死亡;然后他说,“让我们给他们一个永久生育的奖励。”无论这个人活多久,他都和20岁一样有生育能力。这大概是你能要求的一切,不是吗?
梅达瓦指出,即使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的生活也会改变很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过着人类的生活,就像我们习惯的那样。每次你过马路,你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有汽车,卡车,火车,飞机;有病毒和细菌。它们也需要生存,它们还会继续工作。还有电路,和其他的危险。所有的保险精算师需要做的就是等一会儿,很快他们就会给你寄来新的费率。梅达瓦说,事情会改变得如此之少,可能我们现在的老年和死亡的模式,本质上是遵循不可避免的模式,如果我们事实上是不朽的话。
所有这一切的奇怪之处在于,我们已经拥有了不朽,但在错误的地方。我们拥有的是生殖细胞;我们想要的是体细胞,身体。我们爱上了身体。那是从镜子里看着我们的那个东西。那是你一生都在追逐的那个可爱的身份的存放处。至于那个有可能不朽的生殖细胞,它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后在哪里,我们几乎不感兴趣。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我不再这样想了。你看,今天在地球上活着的每一个生物,都代表了一条从第一个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原始生物开始的、没有中断的生命线;那是大约三十亿年。那真是不朽。因为如果那条生命线曾经断过,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所有这些时间,我们的生殖细胞一直过着那些单细胞生物,原生动物的生活,通过简单的分裂来繁殖,偶尔经历一次合子形成的过程——两个细胞融合成一个——在性繁殖的行为中。所有这些时间,那个生殖细胞一直在制造身体,并在死亡的行为中抛弃它们。如果生殖细胞想在海洋里游泳,它就制造了一条鱼;如果生殖细胞想在空中飞翔,它就制造了一只鸟。如果它想去哈佛,它就制造了一个人。最奇怪的是,我们身体内携带的那个生殖细胞做过所有这些事情。有一段时间,几亿年前,它在制造鱼。然后在一个后来的时期,它在制造两栖动物,像蝾螈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更晚的时期,它在制造爬行动物。然后它制造了哺乳动物,现在它在制造人类。如果我们只有克制和明智,不去干涉它,天知道它在未来的时代会制造什么。
我也曾经认为,我们的不朽在错误的地方,但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认为它在正确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不朽——而我们拥有了它。
本文译自 elijahwald,由 BALI 编辑发布。